联觉、比喻与象征空间
【编者按】
《如此陌生而奇异:感官与审美的地理学》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集中探讨审美的一本著作,展示了感觉与美在我们的个人及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美不仅仅是文化的一个侧面,而是居于其核心——既为其驱动力,同时也是其终极目标。全书的探索由个人与其物质世界的关系开始,随后一步一步深化,从对构成审美体验的基本要素(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逐一检视,逐渐过渡至对更广泛、更复杂的人类活动的探究,包括艺术、建筑、文学、哲学、音乐等。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新行思授权发布。
感觉与审美之间的差异——不加思索地生活在多种感觉的环境中,与专注地运用一种特定感觉模式之间的差异;较为随意的日常感知与探究性鉴赏之间的差异——反映了思维发挥积极作用的不同程度。在这一连续渐变的范围中,审美体验占据了其中间的一大部分:过多的情感,对日常生活的过度沉浸,对单一感官模式的过度专注,或对抽象思维的过度运用,都会削弱甚至破坏它。
本章和下一章将探讨两种多感官现实。两种都很复杂,一种由身体经验,另一种由思维构建。一种是自然事实或未经规划的建筑环境,另一种多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创造。世界之所以具有多感官刺激性,不仅是因为它本来如此,还因为我们人类是这样规划它的。由此,我们将首先考虑未加思索的经验和生物事实,然后逐步转向更复杂的人类创造——从联觉中多模态的体验,到创造性地使用隐喻和明喻时的混合经验模式;从基于对隐喻性语言和图像能力的深刻理解而构建的象征空间,到极其复杂的美学—道德状态的构建。
多感官体验
我们对近处环境的体验是多模态的。近处的事物可以触摸,或许还可以品尝、嗅闻、聆听和观看;它具有一种现实的稠密质地,这种现实是由长期持续的多重感知所确认的。然而,随着距离拉远,各种感官会逐一失去作用:首先是触觉和味觉,然后是嗅觉,接着是听觉,直到最后只剩下视觉。随着距离观察者越来越远,知觉领域在“变薄”:在鼻子嗅不到气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耳朵还能分辨出低沉的车流声;再远一些,声音慢慢淡去,只留下一个寂静的场景。距离越远,世界看起来就越简单,人们也就越容易以评估—审美模式而不是“沉醉”模式来感知它。在这种情况下,心理距离和地理距离存在一种平行关系。难怪人们普遍认为视觉才是真正的审美体验。在近距离环境中,心理上的距离很难拉开,因为在那里,人们往往会被感官激起的情感所征服,还因为当几种感官同时发挥作用时,需要特别努力才能注意到一种效果而不是另一种效果,或者它们共同构成的复杂微妙之处。
尽管如此,只要刺激不是过于强烈,我们还是能够从美学角度欣赏近处环境中的某些物体。壁炉中的火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火是色彩和运动,是噼啪作响的声音、香味和温暖。火仿佛有生命一般,它能够按摩和刺激我们的大部分感官,让我们感觉自己还活着。但我们也可以充分地抽离,把它作为一个客体来思考。当我们深深地靠在扶手椅里,灯光调暗,窗帘关上,我们在燃烧的木炭前奢侈地烤着火,呼吸着它的香气,听着火焰温柔的噼啪声,凝视火焰的舞蹈。跟炉火不同,乡村不仅仅是环境中的一个元素。它就是环境,同样也能提供多感官刺激。如果我们不熟悉乡村,可能会主要关注其视觉特点;但如果我们熟悉乡村,对它习以为常,那么非视觉的特质就可能凸显出来。约翰·考珀·波伊斯(John Cowper Powys)是这样说的:
设想在下一个无事的夏日午后,你悠闲地漫步在一片怡人但也平淡的风景中。你将立刻意识到的——且比你对任何色彩或形状或声音的意识要强烈得多——是那一天的气味。接下来,在你的注意力集中到任何一样特定物之前,你会生动地感知到那一天的触感。我指的是空气的冷或暖,你脚下土壤散发出的冷或暖,尤其是风吹在你裸露的皮肤上的感觉。但第三点是最关键的:那一天的味道。
波伊斯所说的“味道”是各种感官的综合魅力,或者用他自己的更实在的话说,是“反复咀嚼感官的满足”。
联觉与联觉倾向
联觉是一种奇特的生理—心理反应,仅部分依赖于外部刺激。当一种感官模式(如味觉或嗅觉),刺激激活了另一种感官模式(如听觉或视觉),这就是联觉。一种常见的联觉形式是“彩色听觉”即听到一个声音的同时产生一种色彩的视觉。人类话语中的元音激发的彩色图像具有惊人的连贯性。音高与图像亮度之间的联系更常见。例如,低沉的嗓音、鼓声和雷声等低音会产生黑暗的图像,而尖细的声音、小提琴声和女高音则会产生白色或明亮的图像。另外,音高与图像的大小和形状之间的关联也很常见。高音细小、尖锐、锋利,而低音深重、浑圆、巨大。
联觉是高度个人化和具体化的。有人曾对弗朗西斯·高尔顿说,在他看来是,字母A总是棕色的。而对诗人亚瑟·兰波来说,A却是黑色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自幼便具有(或说患有)高度的音色联觉。对他来说,英语中的长音a带有“枯木的颜色,但法语中的a则让人联想到抛光的乌木”。有一位俄罗斯记者说,每一种声音都带来光和色的体验,有时还会带来味觉和触觉的体验。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他说:“你的嗓音多么的清脆,多么的黄。”联觉增强了这位记者的记忆力。他遇到的每个物体都深深印在他脑海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虽然只有一种感官受到刺激,但其他感官也同样被激活,于是便加深了他的印象。当这位记者离开他接受记忆测试的研究所时,一位科学家无心地问:“(下次来时)你不会忘了回研究所的路吧?”“瞧您说的,”这位记者回答道,“我怎么可能忘记呢?不是有这道栅栏吗,它有种咸咸的味道,手感很粗糙;它还有种特别尖锐刺耳的声音……”
真正的联觉很罕见;但联觉倾向——一种感官受刺激后,会引起一种与其他感官模式相关的情绪——是很常见的。纳博科夫称法语的a像“抛光的乌木”,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诗意的幻想或一种特殊心理紊乱的表现。但另一方面,我们大多数人又认为把鼓声或雷声这类低音与黑暗联系起来,把高亢或尖细的声音与白色或明亮联系起来,并没有什么奇怪。高音细小、尖锐,而低音巨大、浑圆,这一点我们也并不觉得奇怪。真正的联觉者在听到滚滚雷声时,会真的看见一个黑暗的图像——一个黑暗的形状。而我们其他人只会感觉到声音以某种莫名的方式给我们带来了“黑暗而巨大”的感觉。
查尔斯·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的研究表明,联觉倾向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中广泛存在。在对英美人、纳瓦荷人和日本人的一项研究中,他发现三个群体都会感觉“快”是轻薄、明亮和弥散的;“重”是低沉、阴暗和距离近的;“安静”是水平的;“喧闹”是弯弯曲曲的。世界的“感觉基调”似乎在任何地方都是相似的,不论语言和文化上存在何种差异。
我们尚不清楚为什么会存在跨文化的联觉倾向。部分答案可能在于人们彼此相通的基本身体体验。奥斯古德认为:“当一个产生噪声的物体接近或被接近时,视角的增加是与响度的增加同步的,物理世界原本就有这样的特点。”还有部分答案可能有赖于神经生理学解释。无论原因是什么,我们都是在特定的感觉基调中体验世界的,如果不存在感觉基调,人类的现实就会变得非常贫乏。因此,世界的质感和活力正是联觉的结果。然而,联觉经验本身并不是审美。我们不会特地停下来,对鼓声唤起的“黑暗圆润”感到惊奇;感官的融合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我们早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了。然而,联觉或联觉倾向的心理能力,是隐喻感知、语言改变事物和召唤事物的力量以及(普遍意义上)人类理解和欣赏的原始基础。
隐喻
一个联觉者可能会说一些听起来很有诗意的话,比如说“你的嗓音多么的清脆,多么的黄”,但其本人可能并不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对隐喻和诗歌也知之甚少。人们通常认为,诗歌需要人具有非常形象化的想象力。事实上,诗歌语言中的隐喻唤起的与其说是形象,不如说是意境、氛围和思想。我们说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子“她是一朵玫瑰”。像之前那位俄罗斯记者那样的极端联觉者可能会觉得这个比喻毫无道理。把玫瑰和女人放在一起,哪里有相似之处?比起年轻女性,玫瑰花可能更像卷心菜,但西方文化中的成年人理解这种修辞时却没有任何问题。
幼儿的联觉比成年人更强。这种倾向的生物学优势在于,联觉令物体更生动,更容易记忆,儿童更容易对世界的物质性和现实性产生信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联觉的依赖越来越少,而对灵活的语言资源的依赖则越来越多。儿童的比喻多是感知性的而非理念性的。霍华德·加德纳说,幼儿可能会把修女描述成“企鹅”,但他们并不能轻易理解“铁石心肠”或把爱比作夏日这种心理—理念性比喻。假以时日,进入青年时代,他们将能理解这些修辞,其中有些人还会创造自己的修辞。
语言中充斥着大量静态的隐喻,而使用这些隐喻的人却不知道它们最初如何延展、丰富了意义,也不知道它们对感知和行动继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一点上,那些认为自己使用语言时平淡无奇的人,就跟那些把多感官体验当作理所当然的联觉者一样。一个因习以为常而变得无聊的世界,可以因新的比喻复苏——新的观察、感受和理解方式。当我们遇到或创造出这样的比喻时,我们既能认识到它是全新的,但同时又会感觉到它与我们存在的某些持续的部分相关。尽管一个新的比喻显然是某个人头脑的产物,却似乎根本就不像一种发明,而像一份礼物——对现实的入侵。
某些观看习惯是人类普遍共有的。比如“大地母亲”和“天空父亲”还有以解剖学来拆解地球:岩石是骨,土壤是肉,植物是这宇宙生物的毛发。英语中许多地貌的命名也吸收了这种解剖学参照:比如headland(岬角)、foothill(山脚)、volcanic neck(火山颈)、the shoulder of a valley(谷肩)和the mouth of a river(河口)。借动物来修饰人应当也很普遍。我们用某些简化修饰词来捕捉一个人的性格或行为特点,比如“catty”(“像猫一样的”),“bullish”(“像公牛一样的”),或者“piglike”(“像猪一样的”)。被称作“猪”很让人受伤,就算试图安慰自己“那无非是陈词滥调——老掉牙的比喻”,也无济于事。某些比喻,无论好坏,都能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并具有持久的力量。把某人叫作某种动物,总是会引发某种情感—审美反应,尽管不同动物代表的意义及预期的反应可能因文化而异。
颜色也有广泛的隐喻作用。有些颜色似乎具有基于联觉或共同经验的普遍意义:如红色代表温暖和活力,浅蓝色代表凉爽。有些颜色则传递出不同的意义,取决于它所在的文化背景:例如,黄色在中国是一种代表至高威望的帝王之色,但在西方却似乎充满负面含义——如“You are yellow”(“你是个胆小鬼”)或“yellow press”(“低俗小报”)。还有一些颜色根据上下文语境不同,代表着不同的意义:“你是绿色的”的意思可以是“你很天真”或“你生病了”或“你很嫉妒”。
关于位置的隐喻也是超越文化的:“我是中心”只能表示“我很重要——我是应该受尊敬的人”;“我是边缘的”在任何语言中都传达着一种低姿态。
象征与象征空间
隐喻向后延伸到联觉倾向,向前则延伸到象征:一个方向是变成自动反应;另一个方向是变成文化和积极想象力的产物。象征证明着人类有让一种东西代表另一种东西的能力。象征可以是抽象的、非人性的,比如“用x代表……”,它也可以是有形的、能引起情感共鸣的,比如基督教十字架或一个国家的国旗。对这些抽象或有形符号的理解依赖于丰富的文化背景。与隐喻不同,隐喻可以在灵光一闪之间把彼此并不相似的实体联系起来,并照亮两者,这一过程并不需要更深入的思考,而象征则是类比推理向外延展的结果。柏拉图接受了他所在时代的微观世界隐喻——人体是宇宙的相似物。然而,他并没有止步于这一隐喻,而是着手建立了一整套宏伟的关系模式,试图协调从极小到极大的宇宙各组成部分,并在这一过程中将人体变成了一个多层次的象征。
象征空间贡献了一些人类想象力发挥作用的很好的例子。当空间将人类和社会事实与自然事实紧密结合在一起时,它就变成了象征性空间。象征性空间是一种精神造物,是生活秩序的必要构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实用的尝试;但它也始终饱含诸多美学价值,如平衡、节奏和情感。符号空间有不同的基础,规模大小也各有不同。有些空间的基础是中心—外围的网格和基本方位,其尺度小至一枚神圣烟斗,大至一个国家,这类空间似乎都与人类的实践、思想和想象息息相关,因为这种空间遍布世界各地——新世界、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欧洲、中东和亚洲。无论它出现在何处,其中心与基本方位的空间框架都包含其他象征,可能包括颜色、动物、季节或气象现象以及人类社会类别与社会活动的组合。不同社会的复杂程度不同:规模更大、更复杂的社会往往拥有组织更清晰、装饰更精美的空间。个体能站在象征空间之外并保持充分的距离来欣赏其规模、意义和美感的程度也不同。在每种文化中,只有少数人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教师的角色,能够自如地用语言表达群体的价值观:根据文化的不同,他们可能是巫师、药师、朝臣或学者。但该群体内所有参与仪式的成员应当都对正在进行的活动——比如朝太阳升起的方向祈祷——有一种感觉,伴随着一种恰当感,一种事情做得很令人满意、很正确的感觉,一种受福且美好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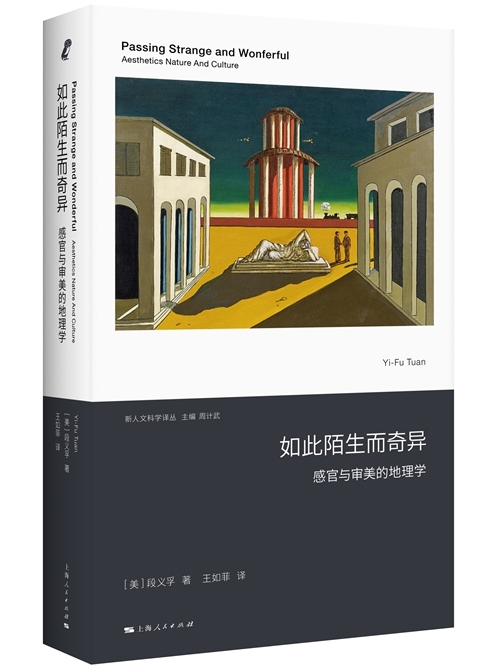
《如此陌生而奇异:感官与审美的地理学》,[美]段义孚著,王如菲译,新行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









